说实在的,谁又会对这件事儿感兴趣呢?知道了他们所说的语言后,然后呢?跟我有什么关系?对我有什么影响?有什么用处?
一个离我不太远的太平洋小岛,我却从来不晓得它的存在。在我逛 Berlin – Humboldt Box博物馆的时候,才知道在地球某个角落,有个名叫Ambrym的地方。Ambrym 是属于Vanuatu国的一个小岛。Vanuatu国有234000居民,操着100多种语言。而Ambrym西部人所说的语言,全世界只有一千个人在用。这个语言虽然濒临绝种却依然有着传承下来的一丝希望。当地人在开始学国语Bislama语的时候,也构成了丢失自己语言的因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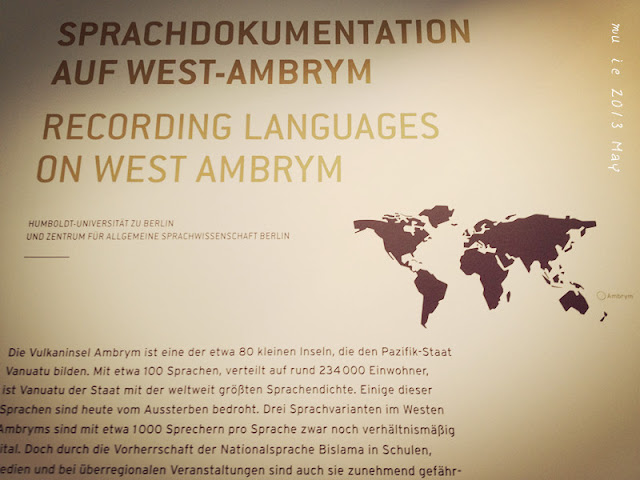
先别说Ambrym。想起了和我居住在同一片土地的原住民。在沙巴州居住的原住民至少有30个种族,而我认识的民族很惭愧地告诉大家只有六种。以前小时候还错把他们和“马来人“归为一类。母亲大人一直在教会的“马来文堂”服侍。当我稍微长大的时候,好奇着去参加“马来文堂”的人是谁?“马来人”不是一般上是穆斯林吗?怎么会上教会?参加“马来文堂”的根本不可能是“马来人”啊!后来明白了,他们只是用“马来文”为媒介语,他们不是“马来人”。从此,我学会了新词“原住民”。
在德国时认识了J小姐。J小姐是沙巴原住民之一的Rungus女孩儿,她来德国半年观摩德国幼儿园的理念以及如何操作。好学的德国人喜欢让我们介绍我们的家乡。当我们在解说马来西亚人口的时候,我喜欢强调“J小姐是马来西亚人口11%(原住民)的一小部分,世界之大能认识到一个Rungus人,你们实在太幸运了!”
J小姐也常感慨着Rungus语言的消失。很多Rungus家庭只说英文和国语马来文,为了提高孩子们在残酷社会力争上游的竞争能力,而牺牲了小孩学母语的机会。她回忆儿时晚风下年长妇女给小孩儿们用Rungus语诉说着古老故事,一切只能记忆中回味了。一个语言的命运,就因为被认为不重要,就没有了生存条件。
 |
| 同行的Anni。资料以文字、实物、大屏幕呈现。拿起耳机还可以听到“语言录音”。 |
时隔千年。假设Ambrym西部人掌握了对世界和平很重要的知识,Ambrym西部人说的语言就会流行起来,全世界开始关注Ambrym西部的文化和语言。还是联合国会建议他们学些国际语言,如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等,便于交流?或者世界对“世界和平”也其实并不那么感兴趣?